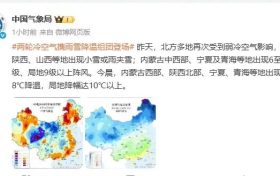【撰稿:袁正强】岁月如梭,时光荏苒。逝者夫,难释怀。在关口坝的日子,60余载弹指一挥间。陕西省宁强县关口坝,那个在云朵上的小镇,百年前羌族人在那里聚集开垦繁衍生息,红四方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,我的金色童年憧憬美好生活的一方热土,至今让人怀念留恋,记忆那失去的轶事。那条古老的街道,那一桩桩一件件往事,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,勾起许多美好的回忆……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关口坝位于宁强县版图的南端,曾经是宁强县巴山区委,区公所的所在地,总面积429.59平方公里。接壤四川省广元市两河口十余华里,东接汉中市南郑区黎坪,山大林深,崇山峻岭,高寒气候。在宁强县境内属于“老少边”(革命老区、羌族居住地、边远艰苦地区),自然环境艰苦,交通不便,经济条件落后,面积大人口较少,距离县城约70里路,中间横立红石梁、照壁山相阻隔。从县城到关口坝,要途径金家坪、后河、翻越南山红石梁,过茅坪沟,爬跨照壁山,然后步行穿越十多里的山川才能到达关口坝。不通公路,凡在那里工作的干部职工教师,医务、工商、税务等公职人员都要跋山涉水,到达工作岗位。关口坝的日用生活用品、生产资料、医药、文化课本、体育办公器材等一切物资,要人力运输。当地的山货、生猪、蛋类、土特产靠人力背运到县城销售。来来往往离不开“运户”。常年累月运输货物,关口坝、茅坪沟有一支专业运输队,全是身强力壮的小伙子,脚力超过常人,背一百多斤的货,翻山赛过一般人,走平路健步如飞。人们的书信、邮寄,凭每日邮递员传送,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仅靠几部座机电话。宁强县邮电局每日固定三四个专人专程传递关口坝、茅坪沟、大竹坝、毛坝河、禅家岩、三道河、黄坝驿几个线路的书信邮件和报刊、杂志,民间称“巴山鸿雁”,人民邮电。关口坝虽小,作为巴山区委、区公所以及关口坝人民公社的所在地,其党政行政机构和社会服务功能基本完整配套。
那是1963年的一个寒冷的冬天,宁强县北关小学已放寒假,年庚将至,我刚9岁小学三年级升四年级。有一天,忽然我的母亲许明英从巴山供销社打电话到县城河街工商联办公室,要我次日随巴山一个“运户”送我到关口坝,转学到关口坝小学上四年级。当晚,我做好准备,把衣服课本整理好整齐地放进挎包,奶妈刘秀英舍不得我去又没有别的办法,随即领我到北关里吃了二角钱一碗的根面角,一碗有二十个,泼上红辣椒油,熬制的香醋、蒜泥等各种调料搅拌,香喷喷的,色香味美可口,这是宁强百年传统很地道有名的地方小吃,我吃的很香,始终不忘,就算饯行吧,要知道平时很少吃,因为家庭经济困难,穷人家的孩子吃不起。奶妈叮嘱我,到了关口坝,生活不习惯就回来,路上走不动了多歇一歇,雪大路滑要当心,别摔着了。第二天中午,巴山那个“运户”来了,给我奶妈说:“你放心,小娃走不动了,我背他,保证送到关口坝他妈那里。”他说话很客气,声音宏亮,一口巴山腔和四川口音一样,笑哈哈的,平易近人。我仔细地端详着他,年龄二十七八岁,身高1.72米,高鼻梁,大眼睛,炯炯有神,头裹缠黑色丝巾,右侧有一排排竖红色的丝线,扎一束腰带,肩披背帘子,穿一双黄色胶鞋,棕丝包脚,背着背夹子,上面用棕绳绑着一个小木凳,是给我准备坐的,一旦走不动了,就用背夹子背着我爬山涉水。他说姓王,茅坪沟的人,这一路上我就叫他王叔。
我们从宁一中半坡上的围墙口子小西门下山,沿着田间小路南行,直走金家坪辽原队,顺着烂泥沟崎岖绵延的小路,到了后河里。后河河面宽30多米,流水清清,水深膝盖,河面有搭好的石墩子,不用脱鞋踩水,一步连一步的跳跃式跨过后河,走过几华里丘陵山坡,开始翻越红石梁。红石梁,赫赫有名。县城南望,人称南山,巍峨屹立,一眼望不到边的红石梁,郁郁葱葱,不寒而栗,肃然起敬,民间有“抬头见南山,悠然在乡间”之说,山上树木参天,藤条荆棘,遮天蔽日,竹林遍布。多以冬青树、松树、马尾松、青杠树、漆树、板栗树、柏树、樟木、桦木树、还有水杉树、刺槐、五倍子等,也有一些药用树种。一片片竹林,多为小径竹类,品种有松花竹、箭竹、木竹等。灌木丛生,枝繁叶茂,一望无际,漫山遍野,原始森林。半山悬崖,有一些小溪,水流湍急,潺潺流水,山间泉水叮当,巨石斜立,横七竖八。这条茶马古道,山路弯弯曲曲向上盘行,静悄悄的,偶尔林中飞出几只野鸡,扑通通的在树林中飞翔,打破空山的宁静。追随其后的是一只金鸡,拖着长长的金黄色尾巴翎毛,一跃斜飞天空,身上的羽毛呈褐斑色,个头不大约三斤重,颜色艳丽,飞翔的速度快,敏捷灵活,听觉性强,稍有风吹草动,或者森林中有人的脚步声和其他陌生动物的声音,它闻讯后立即飞往另一安全地方觅食栖息。
翻红石梁山顶,从半山腰至山顶白雪皑皑,山路树林白雪一片,积雪深一尺多,一脚踩下去软绵绵的到膝盖,银装素裹,天上飘着雪花,不见行人。我实在走不动了,“运户”王叔把我背上坐在背夹子上的凳子上继续前进。他绑上脚码子防滑,走上一百多米,用搭杵子顶住背夹子歇一歇。翻过山顶,他叫我下来走路,坐的时间长了脚冻。于是,我跟随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往山下走。俗话说:长不过四月,短不过十月。虽说是腊月天黑的早,到了茅坪沟,又走了一段乡间小路到了他家里,天色已黑定了,伸手不见五指。他家座落在距离公社三五华里,依傍小河500多米的田坝,三间土墙盖瓦的房子,侧厢厨房,猪圈盖青石板,前面土地面院坝,房前屋后自留地种菜,雪地一片不见绿,小河结冰,冬水田结冰积雪覆盖。到了他家门口,我俩拍打衣服和鞋上的雪走进中间的堂屋,他媳妇热情地招呼我们,倒了一杯开水,叫我们围着堂屋地火炉烤火。山里习惯烤柴火,堂屋西侧土墙旁,四周用石条围个正方形,干树桩疙瘩堆在墙边,中间架起青杠柴,上方吊一鼎锅煮肉、做饭、烧开水。他媳妇二十多岁,身高1.6米,一身羌族人的打扮,头缠黑丝巾,腰围绣花围裙,脚穿绣花黑布鞋,耳坠银环,她和王叔一样服饰穿戴是典型的羌族人。端上桌的是两碗面条,没有干拌酱油、醋、辣椒、蒜、盐,也没有臊子或者浆水汤,饿了端起面条就大口大口的吃,随后又端来了两碗米饭。王叔用面条下米饭,津津有味。后来我才知道,来了贵客,主家才下面条吃米饭,面条就是下饭菜,过年也是这样。
第二天下午,我们启程翻越照壁山。照壁山,高耸入云端,在山脚下仰望,东西无边际,高高矗立横亘,遥望红石梁,相互呼应。中间狭长地带茅坪沟,北风呼啸,雪花飘飘。好一派北国田野风光。
茅坪沟是红色老区,1935年红军在这里设红军医院和军械所。同年,茅坪沟人何锐、马连理参加红军,经过长征,屡建战功。开国授予红军何锐上校军衔,曾任中央军委直属疗养院副院长,西安陆军医院副院长职务。马连理参加了辽沈、平津战役。建国以后,曾任天津市南开区公安分局局长、区长、区委书记、人大主任等职务。
房上田间地头,山上山下,一片银白色苍茫。照壁山半山腰,明崖突兀,冰柱倒挂,晶莹剔透,雄姿壮观。远看似一幅冰雕艺术珍品,具有极高的自然风光欣赏价值。我杵着一根木棍子,跟着王叔爬照壁山,山脚至山峰中段地势延绵盘缓,弯路不多,山势走向顶端陡峭路窄,直行攀爬,十分艰难。有的地段悬崖峭壁,猴难攀爬。我们一鼓作气登上山顶,视野开阔,野草树木被雪覆盖,光秃秃的不见大树竹林。傍晚,夜幕垂降,我们到了关口坝,王叔把我亲手送给我母亲许明英,道谢后离开。巴山供销社饮食员李发贵,喜出望外,亲手给我做了一碗油炒米饭。李师傅个子矮,30多岁,家住宁强县城关区金家坪公社辽原队,平时没有客人,看到从宁强远道而来的小朋友自然亲切高兴,问寒问暖。
关口坝街长约400米,宽20多米,街面一段铺青石板,大部分为土路,民居古香古色,南北分别座落两排民房,木排扇盖青瓦。从东向西,一条小河环绕街道半弧型向西一直流往四川旺苍县境。街道北面札河堤一米多高,一块厚重的大石板铺架河堤两岸,连接高桥队通往关口坝街道。很早以前,关口坝居住的是羌族人,在这里繁衍生息耕作,如今的关口坝人带有许多羌人的色彩、服饰、口语、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、婚丧嫁娶、民间风俗仍然是羌族人的生活模样。关口坝人,民风淳朴,勤劳、厚道、友善、团结、路不拾遗,夜不闭户。民国时期有土匪袭扰之说,解放后无盗抡之话。甚至没有邻里之间的纠纷或打架斗殴的事端。街头是巴山供销社,营业门面四间二层,松木结构,中间小院,建一排木平房,设办公室,会计、出纳、主任、采购员为一体的集体大办公室,共有干部职工十多人,郑作良常住县城负责采购业务,门市部临街,五个女营业员,门市部上面的二楼,青一色的木地板、木门窗。我母亲和大安区的女营业员宋素芳、夏玉林、张必廉夫妇等六、七个人居住二楼。会计黄存鼎,主任张永福等人居住小院一侧的房屋,其余几间为库房,存放货物。通后是一大间厨房,餐桌摆放中间,两张长排木椅,李发贵住厨房旁边的一小间平房。主任张永福,从部队转业为连级干部,对待职工和蔼可亲,每当改善生活,帮助饮食员包饺子、炒菜、蒸馍。会计黄存鼎个子矮,厚嘴皮,大耳朵,圆脸型,工作严谨,为人厚道,稽核商品库存,上报财务报表,从不虚报瞒报。张主任和黄会计在干部职工中评价较高,在基层有丰富的工作经验,营业员对待巴山农民群众,态度热情,使用木杆定制称,出售给群众的商品从不短斤少两,连连受到巴山人民的喜爱,笑迎八方客,送民购货归。每当逢场赶集,供销社是最忙的单位,四邻八乡的农民前来购物,购买食盐、糖、煤油、布匹、鞋袜衣帽等,供销社门市部的营业员,笑脸相迎,介绍商品,帮助农民选择布匹的花色品种,适合什么年龄段的人做衣服,百问不厌,有问必答,农民们非常高兴,十分开心,把她们当做知心朋友,并邀约到家里做客。街道中段是收购门市部,营业员郑克家和老肖,常年累月收购中药材、山货、鸡蛋等农副产品运往县城等地统销。
关口坝街上居住的农民,多以吴姓、王姓以及蒙姓、吕姓。房屋结构木排扇小二层,木板上层放物品,屋内排扇立圆柱,房顶松木椽子盖青瓦,万字花格木窗户,正中堂屋宽敞明亮,一侧地火炉,石条合围,上方吊鼎锅,烤火做饭,属高寒地带,从十月份开始烤火直到来年的四月份,取暖时间长。关口坝昼夜温差大,气候多变。半夜一场雨,正午艳阳天。街道第五间房之后是吕氏住房,门前摆设一口四方型大石缸。中段是巴山区委、区公所、关口坝公社所在地。区行政机构连一体,临街前小院设关口坝人民公社,两排四间平房,通后中部是巴山区卫生院,木板结构二层,过道走廊设中西药取药窗口,对侧面一间设医生问诊开处方室。西医大夫艾玉华,甘肃人,中医大夫郑怀本,巴山人,另有药剂师,护士肖素英、周仕达等医务人员。艾玉华和郑怀本,从医临床经验丰富,虽不是医科名校毕业,但是医术较高,一般常见病,开处方西药不多但很快见效。郑大夫擅长中医,不是科班出身,可是看民间疑难杂症在行,当地老百姓找他看病的人多,以“赤脚医生”闻名百里。这俩人在巴山地区很受百姓爱戴,无论天晴下雨,深更半夜,群众上门,随叫随到,如遇急诊跨个医疗箱,打着手电筒或提着灯笼,一块跟群众上门看病。孕妇临产急诊,艾玉华和护士肖素英上门接产,直到顺利生产,母子平安才放心。熬了一夜,群众十分感谢,煮上一碗热乎乎的荷包鸡蛋,表达感谢之情,不然说啥也不让离开。在老百姓的心中,关口坝有两个好大夫:西有艾玉华,中有郑怀本。不是神医胜似“神医”。文革期间,艾玉华调回甘肃省大庆市,老百姓依依不舍,含着热泪主动送别。送君送到坝街口,男女老少不叫走。今日一别何时见,也许来生才相逢。艾玉华、郑怀本、周仕达的名字,在关口坝人民群众的心里是座无名丰碑,没有锦旗,没有奖状,没有医学博士的头衔,没有主治医师专家教授的光环,但是巴山人民在民间认为他们医术精湛,医德高尚,名不虚传。
巴山区委“大院”,座落在卫生院径直通后,相对于关口坝的地域称之呼机关大院。南北两侧,修建两排平房,一排平房约十间,每间十多个平方,砖木结构,青一色的蓝色门窗。窗户安装玻璃。南面平房为区委、公社书记和干部、巴山派出所民警居住,关口坝公社书记龚正美住第二间,第三间居住我的父亲袁俊,时任巴山区委书记。北排平房,前三间为巴山营业所金融机构,中间是区委区公所办公室,末端居住武装部广播站和农技干部,院场中间种菜、植树。区委办公室门前块大石板,四个石墩,休闲时机关干部作为看报、下象棋之用。区委书记的办公住宿和其他干部一样,办公住宿合为一间,室内门口窗下摆放一张带抽屉的办公室,桌上堆放文件,一张玻璃板,陈放马恩列斯毛著作政治经济学等书籍,墙上挂一幅毛主席的画像,里面一张床,一个脸盆木架,一把靠背藤椅,条件十分简陋。除过随身的衣服、床单被褥,别的没有什么物品。区委院场后方台阶上面是大会议室,四间平房的面积,主席台摆放两张长方形桌子,铺蓝色桌布,墙上挂马恩列斯毛的画像,会场中央摆放双排木长条排椅,通后是三间厨房,连着餐厅,几张桌凳。厨房紧靠山坡,一根半圆大竹子连接山边一条溪水沟,大木桶接水,一年四季供区委区公所公社卫生院的日常饮用水,干部大夫用茶壶、水桶提水。区上饮食员张满清,宁强县城关区金家坪公社人。区委办公室干部李长春,30多岁,瘦高个,性格开朗,喜爱下象棋、打篮球。平时区委领导和干部经常下乡蹲点抓生产,通知开会回到区委大院,显得热闹活跃有气氛,区委大院众多大小单位,只有一个大公厕,修在北面房后,前面长着一棵大核桃树。临街中段就是邮电所、工商税务所,关口坝不通电,单位安装一部电话,夜间照明通用煤油灯。区上开大会,放电影时,柴油发电机发电照明。关口坝街尾,设关口坝六年制小学。校门口立红军石刻标语,红色字刻醒目。学校共有校长、教务主任、教师十多人。校舍条件十分简陋,共有二排教室,两个年级同在一间教室上课,三年级和四年级为一个教室,一个老师先给三年级学生讲课,布置作业后,又给四年级的学生讲课,音乐体育课,一个老师合并给上课。教室门前为简易篮球场操场。老师办公备课设在学校北侧,集体统一办公,旁边为老师宿舍食堂。南边靠田野一角为学生自己做饭洗衣服的地点,六年级住校生较多,学生宿舍紧靠教室。多数学生中午自己做饭吃,距家远不住校的学生自带干粮。宁强县城南街人马冀,原逸夫中学老师李哨峰的母亲周老师,在关口坝学校任教时间较长。
关口坝赶场,集市贸易人多,手推机拱车,骡马驼货,人来人往,熙熙攘攘。早晨,从四川邻界来的人,背着背夹子,带一条狗随行,刚从街尾踏入街道,关口坝的狗,咬个不停,随着信号的发出,街上一拥而上四条黑黄色狗,围着川人狂叫。它们好像是关口坝街上忠诚的卫士,欺外狗仗人势。可是,遇到街上人,不管是大人小孩从不欺咬,童叟无欺,护主忠心。街头段堆积木炭、青杠柴、竹椅木凳。鸡鸭生猪等货物,中段蔬菜、鸡鸭蛋、豆制品、黄小豆、玉米珍、粉条、木耳、面条、柿饼、以及中药材、地方土特产。主产小麦、玉米、红薯、洋芋。例如加工成淀粉的土特产五花八门,如凉粉、黄金子凉粉、豌豆、土豆、米粉馍之类。巴山人爱吃浆水菜,入冬每家每户用缸、木桶、杂(制作)浆水菜。吃一个冬天。俗话说:三天不吃酸,走路打窜窜。有腌制腊肉的习俗,年庚杀猪,全村人热热闹闹的在一起吃“疱堂宴”,把剩余的猪肉,用盐、花椒面、酱油腌制三天,挂在火炉上烟熏,讲究的用柏树枝小火熏,肉质红艳艳的,味佳香可,过大年或贵客来了,煮一块,喝自己酿的苞谷酒。巴山人手巧,做人工挂面,人工粉条,可称高山一绝,地方美味佳肴,老幼皆宜,备受青睐。每到月底,宁强县电影公司的巴山放映员席安超,叫“运户”背上电影片子和放映机,到关口坝公社门前为群众公开放映两部电影,十里八乡的农民晚上打着火把灯笼,自带凳子聚集在一起观看电影,看完已是半夜,长长的火把灯笼队伍在山间慢慢消失,随风飘来的是一阵阵陶醉心扉的山歌,巴山人喜气洋洋,堪比过年热闹。
关口坝赶场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猎户,身着羌服,格外与众不同。它们行走在川流不息、熙熙攘攘的人群中,背着大喇叭口的竹背篓,里面背着瘠瘦的麂子(后列为野生保护动物),肥硕的猬子、兔子、精壮的狗獾子,拖着硕长的红色翎毛的山鸡。和猎户结伴而行的村姑,头上插着银或玉的簪子,身上戴着一斛珠式耳坠,胸前罩着绣着花边的围裙,手里提着极其精巧的竹篮,步履矫健地走在男人们的前面,脚下踩着积雪发出轧轧的响声。有的羌人,背篓里背着许多土红色圆圆的根面团团,还有的手提一篓子木耳、香菇。这些山珍是大自然给人们的馈赠,人间美食。
夏收打麦场,男女头顶湿毛巾,防晒防灰,双双排队一字型手里挥舞着连架,把收割的麦子平铺在院坝或关口坝街上,连续“噗咚 噗咚”的对打,节奏感极强,麦粒黄灿灿的顺着麦杆一层一层地掉在下面,扬起麦穗壳几丈高在空中起舞飘荡,尽管人们汗流浃背,却洋溢着收获的喜悦。打一场麦子歇口气,男女边打边对唱山歌,歇气间隙,互相追逐嬉戏,霎时劳作的疲惫与辛劳苦累随之灰飞烟灭去无影踪。秋收,在生产队的仓库院场打黄豆,撕苞谷壳,把苞谷棒子的外壳掰辫纽连成串串,挂在仓库的房檐横梁柱子上,晾干后按家庭人口计算统一分配给社员。
这种场地,是男女青年边劳动,边唱歌加深认识碰撞出爱情火花和感觉,从而谈情说爱,喜结连理的好地方。如果一个青年人爱上一个姑娘,首先要引领唱山歌,姑娘对上眼,双人对唱,倾诉情感。老人和村姑是过来人,知道这些情趣,在一旁挑逗打趣,把山歌对唱推向高潮,生产队仓库的上空传来阵阵掌声,男女老少的喝彩声,浑然一体,连成一片,冲向云霄。这个方式,自从羌人移居关口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陕南地区的农村显而易见,具有地方典型代表性。
关口坝街头的一条小河对面有一座半圆弧走势的山。据老人说当年红四方面军一部驻扎关口坝,在山上挖战壕修工事,用于阻敌防匪袭扰。向北一华里就是关口坝巴山区粮站,两排砖木结构的平房宽敞明亮,用于统购统销贮存粮食、菜籽油,那是巴山人民向国家交“公粮”的地方。每当夏秋,农民们肩挑背扛,排着长长的队伍,争先恐后地交“公粮”,夜幕降临,恰似一条巨龙飞舞,一派繁忙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关口坝有许多红色印记,随处可见山体岩石上“红军是穷人的队伍”,“打土豪分田地”,学校门口石碑,书写着红军石刻标语,关口坝是红军建立苏维埃政府遗址的所在地,据陈英文研究宁强党史撰文《宁强红色资源丰富 未来发展前景光明》一文记载:1933年3月至6月,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、南江、巴中等地粉碎“三路围攻”后,乘胜西进,解放了旺苍、广元大片地区,根据地扩大到宁羌县的毛坝河、关口坝、茅坪沟、黄坝驿等地,1933年8月12日,红三十一军1000多人进驻关口坝,在关口坝、茅坪沟、黄坝驿等地剿匪,打游击,打击土豪劣绅。8月23日,在关口坝建立第一个乡苏维埃政府。
第二年秋天,我转学将要去宁强县南街小学上学,那天半夜四点多钟,我母亲起床给我做了一碗浆水面条,送我走路到照壁山。一路上打着手电,路旁田间苞谷已经收获了,一片片苞谷杆长在田间地头,鸦雀无声。到了照壁山顶,天已放亮,放眼山脚,茅坪沟尽收眼底。母亲叮嘱路上注意安全,平安到达学校报上名给她写封信,依依不舍离去。我一个人往山下走,走走停停转过身,远看她还站在那里遥望,我向母亲挥挥手,转身一路小跑下山,我看不见她了,知道她还要返回关口坝供销社上班,心里沉甸甸的,母子之情难于言表。
1966年,我的小妹在关口坝出生,两年后的一个冬天,父母亲送她去宁强县城上幼儿园。学校放寒假我回到关口坝,也要随行到宁强上学。那时,父亲已经不是区委书记降职一般干部。那天,关口坝天寒地冻,父亲背着她,我和母亲跟在后面走,用绳子绑在鞋中间当脚码子防滑,一路从关口坝走到宁强县城已经是晚上了。那次,是我60年来最后一次离别难忘的关口坝。
1969年10月,国家三线建设正式动工修建阳安铁路。巴山区根据汉中地区和县上的文件精神,成立了巴山区修建阳安铁路民兵团,巴山区任命父亲任修建阳安铁路巴山区民兵团团长。他和区委其他干部以及省下放干部沙荣光,迅速带队巴山区千人修铁路民兵团赶赴施工地段代家坝,和民兵们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,日夜奋战在一线。有一次开山放炮,他在现场组织施工,在掌子面凿眼放炮,炮手一次点燃放炮就是十几个,一炮一炮地都炸响了,等了一会儿不见再响,需要有人去探炮,他和炮手等人逐一排探,用竹竿试探哑炮,不幸哑炮炸响,当场一节竹竿飞起斜射入口腔穿耳,浑身血迹昏倒在地。沙荣光和其他人上前施救,拔出竹竿送往医院抢救,连夜送往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救治。第二天,区委正式通知我母亲从三道河供销社到西安陪护。小沙石冲击了眼睛和脸部手部,做手术转院到陕西省人民医院,经过三四个月的治疗,终于基本恢复健康。党的三中全会以后,全面落实政策,父亲从阳平关医院政治指导员调任城关区委副书记等职务,离休享受老干部副县级待遇。
我随父母工作的变动,再也没有去过关口坝。不过我一直怀念关口坝,是羌人王叔把我背到关口坝,在那里度过一段童年时期的美好生活,成为挥之不去的永恒的记忆。如今,巴山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撤区并镇后,茅坪沟成为巴山镇的所在地,关口坝成为关口坝村。公路交通、公共基础设施有了极大的改善,县城至茅坪沟、毛坝河、关口坝、禅家岩等地通公路、每天班车直达,地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,学校、公共卫生、人居环境以及农业生产等民生各项事业蒸蒸日上,人民群众安居乐业,社会治安秩序好,人民群众感受到了幸福,万众一心跟党走,海枯石烂不变心。
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六日
附:作者袁正强,宁强县政协、县党史办、地方志特聘文史撰稿员。本文属原创,未公开发表。